原创/碧落
听闻麦子已经黄了,看到了在黄灿灿的麦浪里自由飞舞的美丽女子的摄影照。突然很想念家乡的麦子是不是也这样散发着丰收的喜悦?
五一回去的时候,还是绿油油的一片一片,像一幅幅巨大的绿幔平铺在大地的身上。上学上得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割麦,什么时候耕种。这些小时候拿来当节日过的日子,长大后时令已经没有界限了,就好像许多年顾不得想起来的人,偶然一次记起来已经模糊了,连她不在的那一天都可能记岔了。
想象着一片片金黄的麦子,麦芒精神抖擞地望向蔚蓝的天空,好像回到了小时候。
小时候,是个过去词。有些行为动作,只有小时候才会采取,不被责备,其乐无穷。
当麦粒长得饱满却还未硬的时候,我们喜欢去偷麦子,烧烧吃。通常是放学的时候,趁人不注意或者故意留到最后面,悄悄钻进路边的麦子地里。瞅好哪一块麦子长得好,就蹲下来,从麦梢的第一节折断,像聚集花束一样,一根一根地往里面添。左手拿着,右手拽。有时候,为了防止被人发现,会两手并用,把折断的麦头放在地上,折下来的都往地上放。
我们并不是良莠不分,我们专挑颗粒饱饱的,这一块被淘汰,再转战另一块。大约摘到二三十根或者四五十根,我们就跑了。把麦子藏到书包里,或者衣服的里面,假装一本正经地放学归来,什么亏心事也没做。因为我总是想,那么多的麦子,我偷这一点算什么,看不出来的。就算看出来,也不知道是我啊。这种理所当然的心理总让我原谅自己,心安理得地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。
回到家后,欣喜地拿出来,嚷着奶奶:“奶奶,我要烧麦子。”奶奶瘦弱的身体在旁边来回晃动,我们就囚在灶台口,边烧火边烧麦。烧麦的方式有很多种,先用一根麦莛把麦子扎在一起,然后等熄火后,把麦子埋在火堆里,过七八分钟,刨出来。也可以一根一根的在烧火的过程中,放在火上烤。还可以把麦粒揉下来,直接放在锅里炒。最美味的方式是第一种,虽然会沾上柴火灰,非常黑,但是烧出来的麦子香醇味道保存得最好;炒麦的话,香味流失大;一根一根,太少,体会不到大口大口的劲道。
烧好了麦子,麦芒已经成灰,只剩下黑溜溜的麦粒。把它们放在奶奶缸盖子上,两手合并,来回揉搓,像机器一样把麦粒从麦壳里剥离出来,再簸几簸,把麦壳扇出去,或者用嘴对着麦粒吹,吹吹翻翻,同样也能把麦壳清除,留下清白的亮亮的香喷喷的麦粒。
最尽情的享受当属放一大口,慢慢嚼啊嚼啊,那劲道就像吃牛皮筋,有嚼头,有劲儿。麦香慢慢飘出来,溢满整口,还飘香很远,闭眼吸气,品味,好好吃。放少了,味道淡,不耐嚼,还没品到味儿,就嚼完了,不能尽兴。
我们通常吃得像个小猫,长了一嘴的黑胡子,满手黑乎乎的。但是满口余香,回味无穷,也就值了,洗洗就干净了。我和妹妹干这事最多,一般都是我先烧,我先用缸盖,我先吃。我欺负她,可长大后,她却是最舍得为我付出的人。时光不再,我们心照不宣地相依为命。
老乡在微信上说:“我们那儿都忙着收割了,听说小学还放麦假,小时候我们也放过这个假,现在还有。”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放没放过麦假了。
电话哥哥问:“麦子熟了没?还差几天隔?”
哥哥说:“两三天。”
“这么快。”
“嗯,回来吧?”
“嗯,不知道这个星期六下不下雨。”
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看到麦黄、割麦了。其实,我依旧是那个对烧麦念念不忘的农民的孩子。我依然是那个对过去时光恋恋不舍的农村姑娘。


 今天起 微信能转账到QQ了 !
今天起 微信能转账到QQ了 !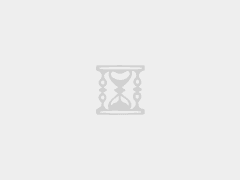
 到底是职位要求,还是就业歧视?
到底是职位要求,还是就业歧视? 今日春分:春耕正当时 莫负好时光
今日春分:春耕正当时 莫负好时光 没有wifi的童年,我们是这样过的
没有wifi的童年,我们是这样过的 从腊月二十六到年初七, 每天陪孩子做一件事, 过一个有趣有爱的中国年!
从腊月二十六到年初七, 每天陪孩子做一件事, 过一个有趣有爱的中国年! 《盗墓笔记》第一季全集
《盗墓笔记》第一季全集 朴实真挚的父子情——《全能囧爸》
朴实真挚的父子情——《全能囧爸》 OpenResty 1.24 支持国密SM2 SM3 SM4(兼容 证签、沃通国密证书)
OpenResty 1.24 支持国密SM2 SM3 SM4(兼容 证签、沃通国密证书) nginx修改server header-自定义版本号
nginx修改server header-自定义版本号 nginx进阶–密码验证(含爆破封禁)+动态白名单 (干货)
nginx进阶–密码验证(含爆破封禁)+动态白名单 (干货)